写在开场的告别
文章发布日期:2018-11-09 作者:汉语言文学专业2018届 李舒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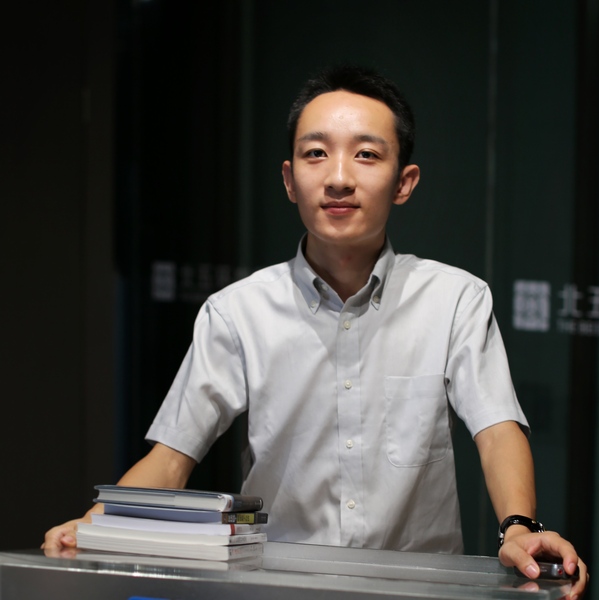
人生是一辆加速列车,许多事根本来不及去认真对待,就要匆匆告别。比如毕业,我甚至以近乎逃离的姿态匆忙离场。所以我要在人生另一阶段刚开场时,作一场关于大学时代的告别。
新生报到那日,我还穿着北方初秋天气里的衣服,站在闷热的泉州汽车站里不知所措。那时怎么也猜不出此后的四年时光会怎样度过。现在回过头来检视,中文系、文学社和小城青年,可以为我大学的所有经历作标签,甚至成为我生命的底色。不过我并不是文学青年,大学里收获的所有感动与成长,也都在文学之外。
中文系
刚步入大学时,我有一种失语的恐慌,不知道在那些泛泛的矛盾的概念之外,还能如何去言说自我。我只知此前胡乱抓本书闷头阅读的方式,是任由头脑成为不同人思想的跑马场,心里很是不甘。所幸中文系有文学史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训练(虽然已简化为用以装点门面的零碎知识点),在各类课外探究及课堂讨论的引导下,还是很快就建立起了一些关于学术与思想的粗浅认知,并尝试着去把它表达出来。
每念及于此,就不能不感谢大学时的诸位老师,尤其是一众热情依旧且兼具学识与见地的青年教师,他们感染着吸引着并引导着我去努力成为一名知识分子。而我的毕业来得太匆忙,匆忙到一切仪式都省略,甚至都没跟师友一一道别,告诉他们在这四年间对我的影响,以及我的何其幸运。
我在大学期间关注思想文化,至少可以追溯到高中时的读书兴趣及习惯,也许换作其他大学或专业,惯性使然之下也会对其有所用心,但郑政老师的经典导读课却绝对出乎我的意料。课程虽名曰“经典导读”,但因课时有限,郑政老师精简扼要,单讲了半部《论语》,大有《论语》专题导读之实。不过她博引历代大家注疏,耐心阐释这些多元的甚至相抵触的义理,而且从来点到即止,不将自己的判断施于学生,从而让我们从中建立起自己的认识。郑政老师让我能初窥经学门径,也切实感受到了其中的理趣,而不再认为经学只是旧时士人皓首穷经后得出的强制阐释,这门课从而弥合了我因文化断层所产生的对古代学者的误读。
还有许多位老师都曾在为学与为人上对我沾溉甚深,尤其是我的导师翟勇。他是给我授课最多的老师,也是我的论文导师,所以翟勇老师贯穿了我整个大学生涯。我耽于建构空疏的概念而荒于基础的文献研究,所以在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往往超出自己应有的驾驭能力而流于粗浅,翟勇老师总能一语点破我在论述中的失当之处,不过惭愧的是我并未能学到他扎实的文献研究能力。而且他又极自律,相比之下生性散漫的我则多次被谆谆教诲,现在虽已毕业却毫无改观,想来仍是惭愧。但翟勇老师为人磊落洒脱,行事不拘一格,我认为这是在普遍谨小慎微的氛围之中难能可贵的品质,在这方面他对我的影响又甚为深远。
我作为一个从来都不甚合格的学生,在中文系终于被老师所“看见”,这种被注视逐渐消解了成长过程中累积的负面压力,开始正面地审视自己的兴趣与能力。
文学社
我毫不后悔进入中文系,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不知道加入文学社是否为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文学社在给了我充足的表达空间的同时,也让我的精力投注到事务上而忽视了思想学术上的进步。所以我把文学社视为诱惑,却又一次次地投入其中不能自拔。
加入文学社纯属意外,当时对文艺理论的兴趣浓厚,而对各类社团兴趣倒不大,只加入了话剧社,因为我认为自己缺乏公众场合自如表达的能力。但宿舍有文学社的学长力邀我加入,我看了文学社刊印的全然是中学生作文习气的读物之后,更是兴趣全无,但拗不过他便注册并交纳了会费。加入文学社之后就是偶尔的跑腿打杂,不过文学社的氛围亲密无间让我很是开心,真正的诱惑是从大二担任文学社主编开始。
我无法准确地描述出当时的境况,总之文学社一时之间全无支持,处理许多事务时往往捉襟见肘甚至几近停顿,我与当时的社长嫣然无数次在讨论文学社该怎么办下去而不至于就此沉寂,不过拮据的境况倒也逼迫着我们想出许多天马行空的想法来应对。
我很庆幸那时能得到文学社其他人的配合而去付诸实现,比如采风、办沙龙、运营公众号、做访谈节目等,当然也有未能实现的,比如排话剧、拍微电影……总之我很享受在文学社做事时虽少有人喝彩却也决无人阻拦的自由,最后无论是实现或者被打脸,总归有个deadline在敦促着前行,否则多数忽如其来的想法会随着其他事情的插入而消散吧。
尤其是“文学·学术沙龙”,我倾注了最多的热情,也带给了我最大的骄傲。在大二时,那种失语的恐慌已经退散,反而有很强烈的表达欲望,而且那时颇为自负,在听了许多无聊的演讲之后,更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文学·学术沙龙”完整记录了我在大学时代的声音,有对底层的思考,有对遮蔽现实的文化幻象的反思,有对猎奇媚俗的生活潮流的解构……虽然关于“应以何种姿态回应时代?”这一命题的立场,一步步从批判走向迎合,但总之都是青年学生在象牙塔里对现实真诚且幼稚的观照,当然也是更深刻地对自我的观照。
现在偶尔翻开当时记录下来的图文,青年的热情与敏锐扑面而来,难免先自我感动一通,那是我的青春岁月啊。“那时候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人们的青春大抵如是,我也如此。文学社让我遇到了许多志趣或秉性相投的朋友,我们会兴冲冲地分享着各自新近的观点或想法,听者或欣然认同,或乐此不疲地辩驳诘难,兴致来时甚至会畅聊至东方既白。
很难想象如果当时我没有给朋友们分享那些议题,那么偶尔的灵光乍现还能否持续深入下去,因为我都是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思路才得以清晰。他们如果流露出浓厚的兴趣会让我有信心继续探寻,他们如果发出旁观者的质疑会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方才的论断。总之,正是他们不厌其烦地听我讲述,才让我不断靠近逻辑上的自洽。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许多偏见也经由他们而悄然间得以纠正。
此外,那些朋友们的热情也在感染着我,给我以行动的力量。比如徐金晓学长,因为热爱戏剧而只身一人创作并导演了部话剧,过程中虽多有为难,但最后公演时在校园也是轰动一时。我后来起意欲办“文学·学术沙龙”时,虽然也面临着窘迫的境况,但想到金晓能独自操办起一部话剧,那我办场沙龙也更应如此。再比如陈颖芳学姐以及她让我认识的一批对教育满怀热忱的朋友,他们去偏远地区支教、为乡村小学募资办图书角,当我还在象牙塔里观察时代时,他们已经在用脚步去丈量文化的转型,也激发起了我尚未泯去的理想与热情。
总而言之,文学社让我在青春里有无数值得骄傲的尝试,不断地试探着自己的潜力与愿望。如果说中文系让我开始感受到了自信,那么对我来说文学社则是中文系的延伸,让我沿着那条能感受到自信的道路继续前行。
小城青年
小城青年这个身份,无论是否喜欢,都被我在大学里彻底坐实,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绝无翻盘的机会。作为小城青年的我,曾经还是对大学生活寄予过很多“他者想象”。比如学校坐落于繁华的都市,然后去经历那些充满着现代化想象的都市生活。或者干脆把自己放逐到荒凉的戈壁滩边上的不起眼的学校,生活简单朴实却又沉浸于精神世界。但那时还太年轻,不知道命运最终只把我从陇东掷向了闽南。
我以逃离的姿态离开平凉,投身到东南海滨城市。日子久了,慢慢熟悉起并喜欢上这里来。在这里的街头巷尾,常见着旧式且色彩极绚烂的衣服的老妇人,她们挑着篮或背着篓,卖头饰上的簪花,卖捕捞的海鲜,卖用糖水渍过的青果……在美丽的校园里,会遇到结满青芒的道旁树,扑鼻而来的栀子花香,许多个天真烂漫的姑娘……这座精致的城市和这所温吞的学校里,我留下了很多关于青春的美好回忆。
生于陇坂乡野的我,经历过几年乡村教育。比如不同年级还得挤一间漏雨的教室里上课、语文课是拿石子在土地上划字、冬日里抱着柴禾去上学……那段经历让我拥有了最原初的感受与淳朴的生命力。后来搬往小城平凉,意味着要融入新的环境也即意味着须反思过去的自己,但融入的同时我却很少能感受到被接纳的认同,索性转而埋头于家里丰富的藏书,通过阅读去超越现实,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
上大学后,虽然也还是在小城里,但也正是因为在小城里,使我能继续兀自成长而不需面临各种诱惑以致自满,当然这都离不开师友们善意的引导和殷切的期望。比如某老师曾一度认为我有成为学术大牛的潜力,鼓励我一定要到一线城市去,并且让我听了很多到访学者的学术讲座。这种有意识的训练让我殊为荣幸,而且在后来也不断显现出那种能力的重要性来。
无论如何,小城的种种让年少的我拥有了一种充满着创新欲望的青春气概,我认为这种生命力是在日渐精致化的时代里弥足珍贵的品质。而我则带着这种在小城里积攒的自信和激情,不断地去试探着自己的愿望与潜力。
也许是毕业离得过近,感念起来牵涉实在太多,以致篇幅冗长沉重,行笔至此也该有个了结。写在开场的告别,尽管是告别,但总要说几句开场白。
年初来京,此时已深秋将尽,蹉跎至此而一无所成。虽然有投身于区块链创业的浪潮之中,觉得那里充斥着各式所谓的理想主义者,实在是再适合我不过,但还是发觉只是一晌梦幻。人生天地间,在不定的命运与未知的走向前,我仍不知会以何种姿态回应时代,但少年心事依旧。
引用第1期“文学·学术沙龙”的一句作结尾:
“向前摸索着出路,我隐约感到了方向,虽看不真切,但希望无所畏惧一路前行,期待遇见更美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