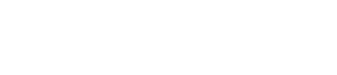蔡崇达:「不忘来处」转过身看自我多深,就能看到世界多远
福建日报新媒体·闽南网记者 陈玉玲/文/图 吴圳烽/视频

蔡崇达,1982年生人,晋江人。2016年创办“立体出版社”“服装品牌孵化器”MAGMODE名堂,开启跨界整合新形态。曾任《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南方国际文学周”联合发起人。曾任职于《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24岁担任《周末画报》新闻版主编;27岁任《GQ》中国版报道总监,为全球17个国家版本的《GQ》最年轻的报道总监。
“我又回来了,如果你们不嫌烦,我就多回来几次。”18日上午,晋江作家蔡崇达在返回母校泉州师范学院时如是说。当天,这位从泉州师院走出去的知名作家,在母校成立了“皮囊文学奖”,并开启了“蔡崇达工作室”工作坊的第一课。


自2014年12月9日出版至今,由蔡崇达创作的《皮囊》销量已经突破280万册。开本比较小的《皮囊》,按照一本本铺开,可绵延530公里。这段物理距离的概念,相当于从福州到厦门,再从厦门回到福州的路程。
我特别感恩泉州师院。
这里是我起步的地方,是抚育我长大的地方。
蔡崇达:
我特别感恩泉州师院。《皮囊》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会,是白岩松帮我主持的。结束后,我马上回师院办了第二场发布会。这里是我起步的地方,是抚育我长大的地方。刚才屈校长说到,在师院读书的时候,很多老师对我“特事特办”、因材施教,这是我非常感恩的地方。

现在说起来你们可能会很嫉妒,当时傅志雄老师是我的辅导员,谢英老师是我的现代汉语老师。他们一路给我开绿灯,还单独给我安排了宿舍,傅老师希望我能写作,写出一本中长篇小说,并在大学期间获奖。那时候,我在学校里写了一本《阿母的手镯》,获得了福建文学小说新人奖。但我现在不会承认这本书,因为回过头来看,它有很多不足。
大学期间,老师们给我很多优厚。不止于此,熟悉我的人就知道,高中时我参加作文比赛获奖,原本要保送北师大,结果在高考前一个月没保送成功。但其实我特别感恩,也特别骄傲,我的大学四年是在泉州师院而不是在北京度过的。恰恰在这四年期间,我找到了自己,也找到了泉州文化。
很多人读《皮囊》,说这很泉州,很闽南。而这些认知,是我在大学期间获得吸收的。泉州有一条江叫做洛江,有一条江叫晋江,因为第一波来到泉州的人是晋朝时从洛阳迁徙过来的,衣冠南渡,一代代中原美好的文化在这里沉淀。当我把泉州看透,也不能说看透,应该是走透了,看到更多东西的时候,我意外获得了很多的滋养。泉州师院在时间和空间上给我很多培养,当时傅老师亲自带队走一个个文化古迹,让我们知道了这些古迹们的前世今生。
刚才屈校长说,泉州师院不是985、211,说实话,你读什么大学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最主要的是能否在大学找到自己,找到和世界相处的方式,自己的内心是通往他人内心,也是通往世界最快的路。
《皮囊》可能是中国这几年纯文学作品销售第一名的书了吧。虽然中国有十几亿人口,销售超过5万本的为畅销书,超过10万本的为超级畅销书,超过30万册的基本已经凤毛麟角。这几年超过百万册的,没有几本,我所知道的可能就是柴静的《看见》,再有可能就是《皮囊》了。

这也是我很开心、很骄傲的地方。在我看来,《皮囊》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而是我从这片土地汲取的力量。我设立这个奖,很重要的是想告诉大家,你在这里同样能找到世界、征服世界,只是你要找到你自己、找到通往世界的路径。
十几年前,我和你们一样,在文科楼上课,傅老师一方面对我很好,一方面对我很严格,谢老师比较慈爱。每次我被傅老师骂了,就跑去找谢老师诉苦,开个玩笑哈。我去学校食堂排队吃饭的时候,在那立志要写作品、要出书、要拿文学奖、要征服自己想征服的东西。
十几年后,我重新站在这里,回来母校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待。我想告诉你们每个人,你们也可以的,找到了自己的路径,可能就找到了通往世界的路径。我特别感恩,虽然泉州师院不如其他大学有名,但我们学校有很多特别珍惜学生的老师们,像傅老师、谢老师,跟我已经不是师生关系了,我们更像“死党”“好友”,可以半夜打电话聊聊天,包括我跟他们说要结婚了,傅老师也帮我分析了很多事。这就是一群老师给学生灌注的爱,这也成就了我,让我对这个地方充满感恩。
我想对学弟学妹说,好好珍惜这几年,好好珍惜真的认识、爱惜你们的老师,好好找到自己、找到世界,真的希望你们能青出于蓝胜于蓝。我说句不自夸的话,在活着的作家里,我在果麦应该是销售前几名的作家,或许下一任畅销作家就在泉州师院里。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真正的文学,在我看来,不是修饰的学问,它是个人“内心纹路”的学问。
蔡崇达给现场学生带来了第一堂课《回到起点:什么是写作?》。
蔡崇达:
今天时间有点长,怕耽误大家吃饭的时间,我很开心大家愿意留下来听,也特别感谢校长在百忙中陪了我一早上。我一直跟谢英老师、傅志雄老师说,希望能为母校做点什么。中国传媒大学每年都会邀请我去讲讲特稿写作。我在想,既然我已经在泉州师院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总是要做点什么的,我很希望也很愿意,把工作室的工作做得扎实、踏实。

我后来想了想,既然有了工作室,就要开工作坊,我希望这只是工作室成立的第一讲。之后,我希望三不五时来母校讲课,邀请果麦文化帮忙做记录。巴西作家略萨写了一本《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这本书给我的启发很大。我会把讲课的过程记录下来,最后集结成一本小书,叫做《给青年作家的信》,借此做个讨论。
作为第一讲的开头,我想讲讲主题——“回到起点”,今天我回到师院,也是回到起点。那么回到文学的起点,写作到底是什么?只有弄清楚这个东西,才能找到写作之路,或者说写作才能抵达最终要去的地方。
写作是什么?我也一直追问自己这个问题。文学应该怎么理解?“文”,在师院读书的是时候,老师教过我,“文也,通纹”,是修饰的意思。因此,有人认为文学是修饰的学问。这是我一开始得到的信息,在过程中我慢慢发现,从小时候开始认字、老师们试图让我们学会讲事情,到慢慢鼓励我们摘抄一些经典名著,获取更多的词汇量和表达技巧等等,我们慢慢走到一个时间段里,我们会觉得,写作最重要的是文章能有多少修饰,能把修饰弄得多漂亮,也就是文章写得多漂亮,引经据典、使用很多的写作技巧和方式。
实话讲,我在读大学期间,有段时间写得像张爱玲,有段时间写得像略萨,有段时间写得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段时间又像川端康成。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日本文学的“幽静美”。这些都是因为在大学期间,我还在寻找我的表达方式,在找我表达方式的本质,我没有笃定自己方式的前提是,因为还没有掌控我理解到的“写作是什么”。
你们现在一看我的文章,就知道这是蔡崇达写的,是蔡崇达的风格,是蔡崇达的方式。不是所有能写东西的人都被称为作家,不是所有作家都是好作家,不是所有好作家都能写出打动人心的作品。
这里面有什么区别?第一,写作者和作家的区别,任何作家的文字一读就知道是他的,哪怕只是一段话,比如鲁迅先生的作品读一段就知道是鲁迅的,包括张爱玲等等,用我的说法来讲,这些都是来自于原生的表达体系,这个体系起源于驾驭文字、驾驭任何文字技巧、找到感到世界的方式。我经常开玩笑说,如果你让我写刘慈欣老师的《三体》,我肯定完蛋了。上个月,我在北京碰到刘慈欣老师,我说刘慈欣老师如果让你写《皮囊》,你肯定也糟糕死了。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真正的文学,在我看来,不是修饰的学问,它是个人“内心纹路”的学问。那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学习各种语言和表达技巧、结构模型?其实这些都是“术”,学这么多“术”,是为了帮你找到你的道,学各种方式是为了帮你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
我其实在写《皮囊》的两三年前,我才很笃定(自己的表达方式)。在《皮囊》中,能不用形容词就不用形容词,杜绝出现排比句,一般排比句就是当你的内容无法支撑你的表达时,你用情感来堆叠,能不用抒情就不用抒情,能用断句就不要用长句,能用最简单的词语就不用复杂的词语。

我最终形成的文学观和写作观,我经常说,爱是有几万种、甚至几十万种、几百万种的,恨也有几万种、几十万种、几百万种的。人生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它是无比庞杂的,你理解的和我理解的爱,你今天理解的爱和你五天前理解的爱、跟你一年前理解的爱,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所谓词汇,就是试图定义某一种我们共同约定的感受,这种定义从来都是集结的“大象”,很难完成所有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在我看来,文学最重要的是人内心纹路的学问。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同学的提问,阅读重要还是人生理念重要。我们来回想一下,为什么好的文学作品能击破时间,一代代流传。现在的时代,跟小说《在路上》描写的场景和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还会提起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天成地表达这个命题最好的形式。《在路上》这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当时美国的经济受到极大冲击,很多年轻人丧失对现有生活和原有理想的信心,想逃往远方。他们否定现在,对未来和远方投以巨大的想象和依赖,促成了很多美国人纷纷到路上,到远方去。
其实“在路上”的心态,现在也有,十七八岁的你,可能觉得我的家不够酷、我的学校不够酷,你就奔向远方。但那个时代,整个国家塑造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回答“在路上”这个命题最好的材质。他意外地通过写自己的故事,写出这个命题最好的支撑、材料和真情实感的部分。所以在后来,比如我想推翻“在路上”这个命题的表达,已经很难了。

《皮囊》面临的是很重要的现实,中国前几年经历了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大量人口从小村、镇上来到城市,所以有大量告别故乡、到还没抵达远方的孤魂野鬼。《皮囊》有一大命题就是这样的命题。《皮囊》为什么会一直畅销?是因为我的生活本身是由这样的强烈情感雕刻出来的,我拼命地往自己内心找时代、社会、命运、自我一刀刀雕刻我内心的感受,然后我把这一刀刀重新翻译成故事,翻译成最准确的表述,传导出来。其实你也意外的从我身上读到你自己,因为我们作为同时代的人,我们作为人,共同被这个时代的社会、命运、自我在相互雕刻,雕刻出那些命题。
在我看来,其实文学的本质是因为人各有异,人看上去很复杂,但本质上都是被时代、社会、际遇、命运、人性相互雕刻的产物。这个产物就注定了我们有很多命题是共通的。但是命题太细腻太复杂,就像我前面说的,爱有几万种、甚至几十万种、几百万种的,恨也是。所以我仅仅说“我爱你”,你会发现我表达不够,就像偶像剧里经常演的,一方说“我爱你”,另一方说“我知道”,一方又说“不,你不知道”,另一方又说“我真的知道”。这个问题在于,爱这个字表达不了这么多东西,还有更多东西没有被表达出来。在爱的背后还有更深更细更复杂的东西,词语是有尽头的。尽头没有包覆住人的复杂和丰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经常会觉得孤独,因为你的表达真的永远跟不上你内心的感受。
写作最开始,经常都是要先把自己表达出来,突破一个简单的“爱”字,我的爱是什么,我的爱表现为什么,我的爱有多少层次,我的爱有多少不一样的点,我拼命的表达,拼命的表达表达,突破词语的界限,当我试图把它表达出来后,就帮所有有类似情感又不会表达的人做出了表达,他们就会爱你。他们就会说,“哦,真的差一个作家”“他写出了我说不出的话”“原来他写出了我不理解的自己”“读着读着,原来我是这么想的,原来我是这么痛苦的,原来我的痛苦纠结点是这样的”。
其实,文字、词汇只是工具,或者说我相信文字、词汇还会不断进化,进化得更细腻、更准确。我想说这可能是没尽头的,因为人心是无比庞杂的,人心的庞杂程度不斥于整个宇宙,人心的神秘程度不斥于整个宇宙,就跟我们去探索天文学一样。写作就是,你用上最好的工具,开上最好的宇宙飞船,去抵达更深邃更遥远、但真的存在的内心纹路。
人的内心纹路,有可能就是海沟,有可能是喜马拉雅峰,也有可能是喜马拉雅山上一个转折点,小小的一颗可以在极寒地长的小花,它的探索是无比广远又无比细腻的,这就是写作本身。所以你一旦进入写作领域,用我经常说的,叫做“开天眼”。“开天眼”通常是为了看到自己,看到自己后反而能看到所有人,看到所有人后才能看到世界,因为世界终究是人构成的,而人是肉做的,人心是肉做的,每个人的内心都藏着巨大的庞杂的、无法描述又终极孤独的宇宙,他渴望跟你共振,渴望你帮忙表达。
从这个角度来说,写作的本质是什么?是一次内心的探险。就像我们对宇宙有大量的不可知,最终我们用了什么动力可以抵达火星、我们用了什么动力可以抵达更远的地方,这是一步步的,写作也是这样的。我们可能使用哪些词汇、可能使用哪些结构方式、可能使用哪些文学技巧能抵达火星,下一步再抵达再抵达。当你探索出的世界越广远,你也就意外地为人类文明做出点贡献。就像我们想表达哪个文学命题,会引用哪个相关经典,这个经典就像是第一个登陆火星的人类探索者,经典把它描绘出来了。从此人类可以描述这个星球了,可以描述这种情感了,人类可以描述这个命题了,以此为基础,我们建一个空间站,可以进一步探索,写作也是这样。
我们一开始需要学更多词汇、写作技巧,就宇航员一开始要在航天机构学技术是一样的。假设你到了火星时,发现这里只需要一个将氦气转为氧气的口罩就能呼吸时,你就会知道,我全部都不要了,我只需要这个东西。就像我找到了内心的表达星球,故乡和远方、理想和现实、灵与肉,怎么面对人的生老病死,我的语言就不会允许过多的浪漫、过多抒情、过多青春年少的矫情。我知道我要描绘的人性命题是这样的,我为什么会长出现文字的样子,这不是我刻意安排的,在我准备着陆的时候,我知道它是怎么样的状态,知道用什么语言着陆。假如我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作家,我抵达的人性命题星球是一个个浪漫的东西,我的语言就会长出浪漫的样子。写作的本质就是这样的,我长出这样的写作、长出那样的写作,其实都是因为长出来的,都是因为我们要到达的命题催生出来的。
总结一句话,文学就是远比你想象还要广远、丰富、神秘、有趣又非常重要的世界。这个世界甚至也不比探索外太空不重要,其实有可能是同等重要。在我看来,走向自己多深,你就能走向他人的内心多深,就能走向世界多深。在我看来,整个世界何尝不是以人内心的自我发现为驱动的,希望大家从大学开、从现在开始发起对内心的探索,等你试图表达自己的内心,你才真正开始写作。
早在活动开始前,学校就已向广大师生征集提问,最后由蔡崇达回答学生关注热度最高的三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很小的时候就问过自己。当时我为什么会想成为作家,应该说我有点“小忧郁”,内心有很多情感、感受都表达不出来。其实人往往高估了自己的表达能力,当你很生气的时候,最亲密的人问你为什么生气,你说不出来;当你特别难过的时候,爱你的人说你讲出来吧,你就是说不出来。你可能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生气、为什么这么难过,有可能相隔很多年后才恍然大悟,知道生气的原因。很多时候,表达能力是跟不上我们的内心的。
作家是什么呢?是一个刚好能表达或者努力表达内心命题的人。想一想,我们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总会提到一本书叫《少年维特的烦恼》,虽然不一定会看;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会提到一本书叫做《在路上》,虽然也不一定读的完。我们为什么会提到这些书?因为人很好玩,有些东西是不一样的,但人本质有很多一致的命题。这些命题被人表达了出来,我们借出别人的表达来重新表达自己。我另外一个好朋友、畅销作家——大冰,他何尝不是此前的三毛?三毛何尝不是来自此前的《在路上》?我第一次感觉到文学的魅力,是12岁读了一本书《麦田的守望者》,后来又读了《月亮与六便士》。读《月亮与六便士》的时候,我开心地写了一篇小评论,我读到里面的很多章节,全身起鸡皮疙瘩,内心受到极大共振,让我觉得我终于不孤独了,我内心某个细节点的纠结终于有人跟我一样了,还被表达了出来。
我知道《皮囊》的书,有很多是别人买来送给其他人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要嘛就是他觉得内心很多东西表达不出来,这本书表达了,所以他送给在乎的人,希望对方能理解他;又或者就是那个人现在面临同样的问题,他送书希望能试图发声共鸣,帮忙解答疑问。
其实作家天生的责任,就是解释人的内心世界,只是一个很幸运地能表达自我内心的人,在把你的感受表达透后,又很意外地在命题上增加了新的表达力度,很多人会进一步表达,在温暖的位置产生共鸣,进而表达自己,这就是作家的天职。
是闽南这片土地。我就是“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的典范,开玩笑哈。闽南是非常神奇的一片土地,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泉州住着最世俗化的神佛,也住着最神佛化的世俗。在我们泉州,很多人会在庙里打牌、打麻将,输了跑去跟关帝爷撒撒娇“你不是要保佑我吗,怎么让我输啊”。倒过来,闽南土地上的人,很多人小时候会认神明当干爹干妈,这些就像是闽南人的“外挂”。我经常说,你不要得罪闽南人,我们的外挂比你们厉害多了,我们的外挂是神明。
其实我母亲在寺庙当义工,我遇到事情也会到寺庙里坐一坐,坐一下午,不用言语,因为他提供了一个看问题的更高视角。但闽南人不是那种神神叨叨的,泉州人把神明当做父母。阿太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她早早就认识到了灵与肉的关系,早早面对个人和集体、世界的关系,甚至是身体离开后与灵魂的关系,这是泉州人生下来就被摆到这样的思考框架内。我们常说“宝藏男孩”“宝藏女孩”,其实泉州是一片宝藏土地,你们多挖掘它吧。
我觉得阅读就是个人体验,阅读就是最好的个人体验路径,只是你要学会阅读。我觉得很多人不会阅读。应该是初中的时候,我读过台湾散文作家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后来影响了我,文章说“你不要跪着读书,你要坐着读书”,很多人喜欢记很多东西,把书里的东西当做金科玉律,其实不是的,你这是跪着读书。其实书是什么呢?书是一个人很努力、很拼命的想表达他感知到的世界、感知到的人。当你坐着读书的时候,把它当成好朋友,是这个感知丰富的好朋友试图把它感知到的一切跟你进行交流。
我建议的阅读方式叫不求甚解,不用特意记什么。当它分享的东西触动到你,它自然而然会构成你的,帮你打开感受的新路径。如果它不能击中你,说明你们在这个命题上是没有连接点的,也不用强硬记,因为记住的是知识,而不是里面的文化。有知识的文化是不一样的,一定要坐着读书,阅读的目的不是为了记知识,不妨把每本书都当做很好的“路由器”,打开新的感知路径。
但我认为阅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恰恰只有建立在这个情况下,你才能从阅读中找到更好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学会了阅读,你不止是拥有自己的一辈子,还能意外地拥有好多个人的一辈子,因为他们凝结在书上的就是他们的一辈子。除了阅读外,我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个人经验是最重要的,但请大家要真的要生活,真的在经历。我以前常损自己,把一根骨头扔向远方,自己跑过去叼上来再扔向远方。人生不是设定目标再达到目标的,最重要的是体验过程,你在人世间感知到的一切,才是你最重要的财富。
所以说为什么要阅读?因为阅读会帮你开启更多感受的wifi,帮助你在人间看到更多东西。《皮囊》这本书在最后引用了普鲁斯特的一句话“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帮助读者发现自己的内心”。阅读是让你看到你心里永远没有的东西,当你心里经由书里的人生经历和思考,打开了一个个感知点的话,你会发现你看到的世界更大、更丰富、也更饱满和更细腻了。
四年前,《皮囊》这本书要出版时,我在北京办了一场发布会,然后第二场发布会就回泉州师院办,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我文学的起点,也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摇篮。在100万册的时候回来一次,150万册的时候回来一次,200万册的时候又回来一次,本来想在250万册的时候再回来一次,我告诉自己销售每过五十万册的时候,我就回老家做点事情。
今天回母校不是演讲,我们的院长两年前帮我成立了“蔡崇达工作室”,我希望真的来母校讲讲写作课,我很愿意把我以前在写作上的经验跟我的学弟学妹分享,希望在泉州师院完成我对于写作和文学的梳理,我也希望把这个分享给大家,这只是“蔡崇达工作室”工作坊的第一课、第一讲。
我觉得泉州文化是一个很有“根系”的文化,就像这次的主题叫“不忘来处”,我是从泉州师院来的,这里是帮过我、也养育过我的地方,我希望我倒过来自己也成为一部分养分,滋养别人。你回头看自己越深,你才能看得未来越远,只有找得到自己的人,才能找得到未来。
▼
「蔡崇达微博语录」
创造经常看上去像是“无中生有”,其实从来没有无中的有,而是你看不到的“有”,认定为无。
内心共通的人容易相遇,内心不一样的人总会告别。所以就真诚地去珍惜和庆幸。
转过身看自我多深,就能看到世界多远。
当你承担着压力,赶紧借助这种力量,迅速找到并集中到最本质的聚焦点,你会发现,那种压强的力量几乎可以让你无坚不摧。别浪费压力,这是好东西。
不要随着波澜去起伏,事物的本质就如同大海的深处,终究是安定的。巨大的波澜追踪到根部,往往只是本质底部的简单蠕动。
真实是护身符,感知是千里眼。越真实才越有机会走法越准确;越感知,格局的广角才有机会越大、像素越细密。
「不忘来处」
转过身看自我多深
就能看到世界多远
值班编辑:林淳淳
福建日报社(报业集团)拥有闽南网采编人员所创作作品之版权,未经福建日报社(报业集团)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和传播。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gdnZroPMbBAoXuNiE6KiA